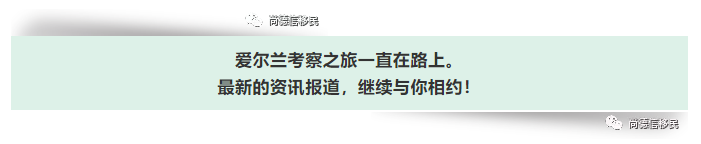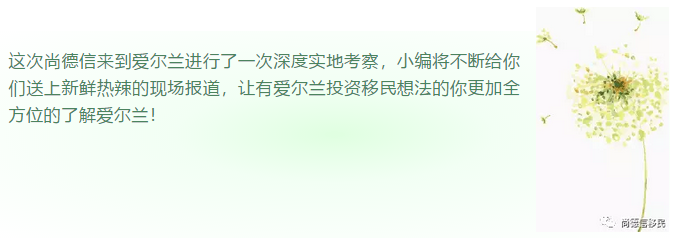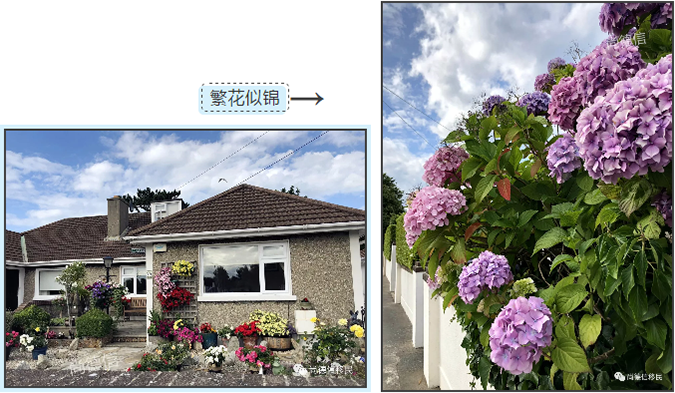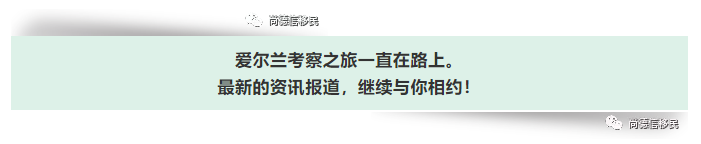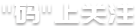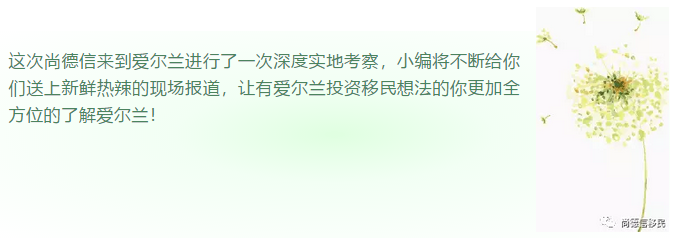

在没有盛夏的爱尔兰,七八月是最好的时节。大西洋暖流和海洋性气候,彷佛凯尔特神话中的精灵,施了魔法般将这个绿色孤岛变的郁郁葱葱。就像校园对青春期的延长一样,在这里七月份仍然是万物生长的春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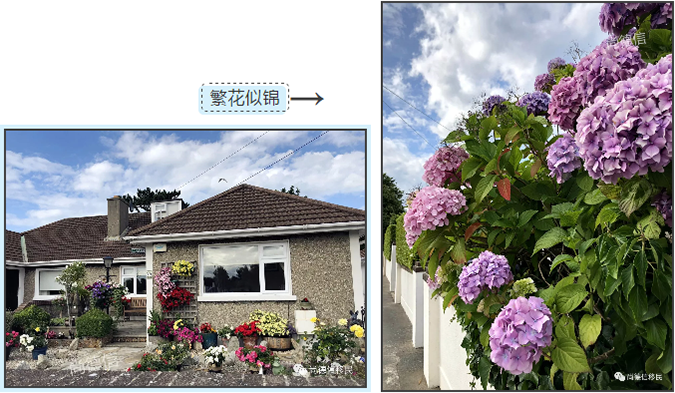
在这个全年最好的季节里,都柏林这座以阴郁、潮湿为特色的城市,终于放下了刻板的面孔,在文学与艺术的渲染下,分外妖媚起来。
经常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之后,瞬间出现灿烂的阳光,雨水冲刷过的街道两旁,乔治王朝建筑的门和路边的花朵,同样的五彩缤纷并且炫目。往往这时会天际会出现彩虹,那是一座桥,连接着天边的另一座城市,那里有一些人和一些幻想。
这仍是一座文字中的城市。
市中心O'Connell大街Eason's书店里,各位爱尔兰文学大家的画像映入眼帘:乔纳森.斯威夫特、W.B.叶芝、詹姆斯.乔伊斯、塞缪尔.贝克特、奥斯卡.王尔德、萧伯纳、希尼......英国人征服了爱尔兰,但爱尔兰人却征服了英语文学。
正是那些文艺青年们的努力,让每一个街角都在《都柏林人》和《尤利西斯》式的描述中熠熠生辉。成千上万的人从欧洲大陆前来消夏,他们朗诵着叶芝的诗歌,观看着贝克特的戏剧,瞻仰者王尔德遗迹,并在街头巷尾追随着詹姆斯.乔伊斯在《尤利西斯》中那18个小时史诗般的脚步。

如果说爱尔兰西部地区体现着叶芝的《凯尔特薄雾》的民俗与魔幻,那么都柏林显然更多的是乔伊斯式的晦涩与多变。
一方面有着英伦绅士般的拘谨,一方面也有着不同于盎格鲁.撒克逊传统的张扬。
那部《泰坦尼克号》中的男女主角在床舱底部跳的是爱尔兰舞蹈,而爱尔兰风笛的声音也贯穿着整部电影。他们是英语世界中的异类,有着拉丁人的热情洋溢。
Great craic!淫浸于盖尔语的爱尔兰口音,像舌头的舞蹈。酒吧里不只有吉尼斯黑啤的醇厚,更充斥着都柏林口音的喋喋不休和手舞足蹈。

在世界的海洋在经济危机中风雨飘摇之际,后凯尔特虎时代的绿岛,依然在一边彷徨,一边饮酒,一边歌唱。
以十八十九世纪建筑为主的老城区在时代的洪流中,看上去不紧不慢,实际上暗潮汹涌。历史保护和城市营销,Boom or Recession,国际资本对城市的注入,城市形态与功能的重组,好似一场精彩绝伦的喜剧。现代的都柏林城市在上演另一幕贝克特的《等待戈多》的困境。

在这个无数游客涌入观光的时节,甚至让人有游客多于本地人的感觉。
故乡他乡,让人迷幻。
圣三一大学绿草茵茵,给人英伦风格大学的震撼,校园里美轮美奂的数百年的老建筑与绿树相互映衬,让回到校园时代,浮生若梦。
维多利亚时期的圣史蒂芬斯公园这个时候每周末公园里都有露天音乐会,会有很多人在草坪上边野餐边享受音乐和阳光。这样的场景总是嵌入在《曾经》(Once)、《闰年》(Leap Year)之类的电影中。

入夏的白昼特别的长,当教堂的晚钟响起,依然是阳光普照。傍晚五六点是最明媚的时刻,在此刻草甸被阳光抚摸出光亮,码头边信天翁在飞来飞去,欢呼雀跃。
直到九点钟之后,暮霭与细雨,光明与黑暗才开始交织,互相刻画着对方的轮廓。

直到夜深了,城市才在寂寥的夜色中睡去,只有串酒吧的年青人依旧无眠。
窗外无垠的草场上,传来窸窸窣窣的的声音。或许是夏虫不安分的低鸣,或许是王尔德笔下为爱情牺牲的夜莺的歌唱。
七月间月朗星稀的天空,让人想起一本书籍的名字,最蓝的蓝。
而我则想起王尔德的名言,“我们都处在沟壑,但是其中一些人在仰望着天空中的星星。(We are all in the gutter, but some of us are looking at the stars.)” 我知道在遥远的天际,有人也正在抬头。